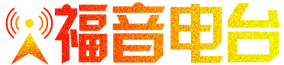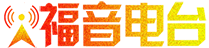十年前的一天, 和一位朋友去寻访故友, 汽车一路颠簸, 来到 我曾经住过十一年的小镇。踏着高低不平满身补丁的柏油路, 到了镇政府的时候, 已是晌午时分。院子里静悄悄的, 一间间房门都上着锁, 手里只有朋友的呼机号, 人已是饥肠辘辘。看到一个小套院里停着辆警车, 应该是有人值班吧。
门上赫然写着110。那个时期, 110和呼机一样,刚刚流行。门没关, 一张写字台后面, 坐着个胖子, 脸蛋子黢黑。一张皱巴巴的报纸铺在桌子上, 两只手摁在上面, 好象在看报又似在赌气。 他看到我们, 眼皮依旧耷拉着, 鼻子里发出一声问话: 干什么的?
我们说明来意, 他的脸上才泛出一丝笑意, 让我们坐下, 给倒 了杯茶水。“哎呀! 今天是星期天, 镇上大大小小的领导, 都回家忙秋去啦!” 他帮我们打传呼, 嘴里还不停地嘟噜, “你们的 朋友,现在肯定在地里呢, 不知带着呼机没有, 就是带着, 回过来, 也得时间啦! 人家都忙去啦, 我还得在这守着。”
端着冒着热气的茉莉花茶, 同行的朋友直摇头,茶是粗茶, 茶杯上还有斑斑的污痕。靠墙的连椅, 漆皮已然剥落, 露出原木的本色, 坐在上面吱嘎吱嘎响, 象医院里排队候诊的病人。胖子进里间屋的高低床上躺下, 大檐帽盖住脸,屋里顿时安静下来。朋友拽过来报纸细细品味, 我穷极无聊, 抬眼看外面的风景。正是深秋时节, 太阳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威, 只是懒洋洋地打瞌睡。
院子里一株脱光了叶的老芙蓉, 消失了馥郁的香气, 只留枝杈上串串风干的树荚, 在秋风中战栗, 几只麻雀还守望在树上, 等候着它们的午餐。一群快乐的鸽子在湛蓝的天空下滑翔, 远远地传来悠悠的鸽哨, 空灵又极具穿透力, 却象远古的女子在怨咽。在眼神恍惚间, 不知什么时候, 门口站立着一个老大娘, 她正用一只胳膊伏在门框上, 嘴里喘着粗气。我连忙站起身, 跨步上前, 用手搀住老人家。老人个子不高, 只到我肩膀部位, 裹着块篮绿色的头巾, 露出几缕花白的头发, 瘦瘦的, 穿一身黑衣, 尖脚打着绑腿。农村人长得老相, 看上去, 应该是接近七十的人了。 她大概眼睛不好, 不停地用头巾擦拭, 这让我想起刚刚从这个小镇接到我那儿住的母亲, 她老人家患白内障多年, 一只眼睛已看不见了, 另一只无风也流泪。
老人伸出另一只手, 抓住我搀扶着她的胳膊, 仰头看着我: “同志, 我有点事想求您!” 她的声音很轻, 有气无力的。我扭头看看了里屋的胖子, 他正半坐起身, 扯掉脸上的帽子。我赶紧扶老人坐在连椅上, 把我的茶水端给她。老人沾了沾椅子不敢坐, 也不敢接水, 只小声的给我说: “同志, 我儿子不见了, 一个礼拜 了, 听说东刘庄轧死了个人, 我问问, 是我儿子不?”
胖子找出个破记录本, 哗哗翻了两下, 不耐烦的问: “说说!你儿子长什么样, 穿什么衣服。” “我儿子, 去年让野狗咬了, 右腿有个大疤瘌, 走路一瘸一瘸的。” 老人用眼看着我回答。
“我问穿什么衣服!” “二妮的娘, 给了他一个红秋裤。他心眼不足, 整天疯跑, 只好让人拴上他, 他咬断绳子也往外跑。原来出去个两三天, 饿急了, 还知道回来, 这回都出去一个礼拜了。” 老人声音软软的, 象是自言自语。“我住在梨树白, 信耶稣的, 今天来镇上做礼拜, 顺便来问问。这孩子看来是没有了。”我的母亲信奉基督教已多年, 看来这是她的教友。
我问了一句: “老人家, 你儿子多大了?” 老人正准备转身离去, 看我问, 抓了抓我的胳膊。“十九了, 就这一个, 是从野地里捡的, 死憨死憨的。唉! 轧死的不是他, 也得饿死了, 他不知道要饭吃。” 老人说话很平静, 已经把死亡看得很淡了。那一刻, 我心里很难受, 从小在农村长大, 对农村人天生的有感情, 我不知道怎样去安慰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尤其是, 她是信耶稣的, 和我母亲一样, 年龄也相仿。母亲目不识丁, “看” 圣经的时候, 非常的虔诚, 天天晚上, 在她的小屋里唱赞美诗, 咿咿呀呀, 象个小学生。她们的一生, 都是浸泡在苦水里的, 以前的苦, 倒给儿女听, 还经常换来一顿呵斥。她们善良, 与人无争, 与世无争, 只是默默的为儿女付出再付出。她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后进天堂, 在耶稣的身边享享清福。 “你瞎罗罗(絮叨)啥!这个死的都四十多啦, 不是你儿子, 快走吧!” 胖子愤愤的回里间屋躺下了。
“大娘, 你老回去吧, 还有七八里路程呢。” 我替老人松了口气, 但愿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正在家里等她呢。老人磨转身, 从腰里抖抖嗦嗦掏出个小布包, 是块方形的小手绢, 一点点打开, 里面包着些零零碎碎的钱, 有硬币有毛票, 看样子也就两块多钱。
“清(早)起来到现在, 还水米没粘牙呢。我买个馍, 吃了再 走。小,你是好人!” 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怕我朋友看见, 摘下眼镜用衬衣的下摆擦擦, 戴上的时候, 顺势抹了一下眼睛。
我把老人搀扶到门口, 问了一句: 大娘, 您老日子还过得去吧? 老人转头看着我说: 我是五保, 队里对我可好了,一月十块钱, 发粮食, 只给我一个人的, 过年还发一张澡票呢。我今天有两块钱“发光”了, 就是给教会了。
老人说到这儿, 脸上明显有了活泛气。我感到,她们这样的老人, 在农村过着贫困的生活, 精神更是无所托付, 但是归了基督, 在耶稣的怀抱里, 不觉得苦了, 就象孩子一样的幸福。
老人颤颤巍巍地, 一步一挪地, 走过圈门, 拐个弯, 消失在午后的阳光里, 瑟瑟的秋风中。她们那一代的妇女, 经历了人世间太多的苦难, 她们只能硬挺着走过, 没一句怨言, 甚至有些麻木了。她们太普通了, 就象地里的土坷垃, 遍野都是, 又象一滴水, 寻常不过。但就是她们, 普通的老百姓, 走过多少风雨, 用一副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属于她们的时代, 有了她们, 才有了沃野千里, 才汇成了浩浩汤汤的大河, 奔流不息。
我的母亲已是78岁高龄, 每日里看书认字, 颂读诗篇满怀信心。 那日邂逅的老人, 看当时的光景, 现在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每当走过基督教堂, 看到红红的十字架, 就好像看到那些与耶稣同行的老人, 她们怀揣着一颗滚烫的心, 不会表达不知索取, 默默地涉过多少艰辛, 现在, 总该是幸福的吧!
《完》